城乡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缓解了健康不平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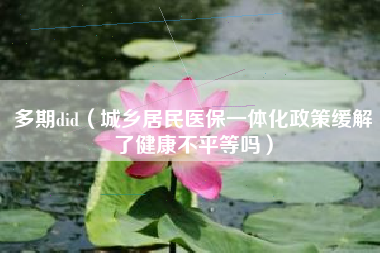
——来自中国地级市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超过5亿的农村居民。长期以来,农村居民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然而,农村居民却没有享受到与付出对等的成果,在获得健康服务方面的弱势显得尤为突出。且健康不平等不单体现在城乡差别上,还体现在收入水平上。高收入群体不仅拥有更好的医疗可及性,同时享受到更多的医疗保障(周钦等,2016;温兴祥,2018),而相对低收入的农村居民群体正面临健康的“双重弱势”困境。健康权是一项人人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拥有平等获取健康的机会。健康不平等程度过高,不仅会影响社会和谐与全面进步,还会进一步引起收入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Baeten et al.,2013),从而给劳动力素质提高、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隐患。因此,着眼于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缓解健康不平等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一项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
医疗保险能够通过分摊患病时的财务风险,保障个体医疗服务利用的财务可及性,起到维护健康的作用(潘杰等,2013;Shigeoka,2014;何文、申曙光,2020)。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可以通过促使个体减少因未来不确定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行为,增加当期消费和改善营养摄入,提升健康水平(Bai and Wu,2014;毛捷、赵金冉,2017)。具有鲜明“互助共济”特征的社会医疗保险能够更大程度上改善弱势群体健康,促进健康平等。为了保障国民健康,中国已经基本建成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国民健康状况不断改善。不过,出于历史原因,中国医保制度体系是基于个体身份设计的,不同身份的个体参加的医保类别具有明显差异(赵绍阳等,2015;Liu et al.,2017),城乡居民享受着不同医保制度的保障,群体间的受益不平等可能进一步导致健康不平等(孙淑云,2015;Pan et al.,2016)。
为了提高统筹地区参保人的医保待遇,缩小城乡医保待遇差距,国内不少地区率先开展城乡居民医保一体化(以下简称“医保一体化”)改革试点,且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迅速推广。当前,几乎所有地区都已经实现了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的整合,医保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已被打破,城乡居民健康得到更好保障(常雪等,2018)。改革后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医保待遇,制度公平性大大增强(彭浩然、岳经纶,2020),但参保机会与待遇水平更加平等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能否缓解城乡居民间的健康不平等,仍然需要更为严谨可靠的实践证据。
基于此,本文采用2012~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三期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集中指数分解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医保一体化政策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本文检验医保一体化政策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补充了保险政策及其公平性对健康不平等影响的研究。其次,本文将总体健康不平等分解为城乡居民群体内健康不平等和群体间健康不平等,相比过往研究更加全面与深入。最后,本文使用了多年度且覆盖范围更广的调查数据,并考虑了制度实施模式和时间的异质性,从而能够为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的完善提供更具指导意义的现实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政策背景
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为了尽快实现人群全覆盖,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根据人员身份进行设计的。尽管这种设计理念加快了制度的普及速度,但是制度分割、人群分割导致了公平和效率的双重损失,并妨碍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医保制度的建立。
2016年1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要打破医疗保障的户籍分割,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一些地区为更好地保障参保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率先开展了医保一体化政策的试点。这一渐进式推进的改革特征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该数据库涵盖了中国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的29个省(市、区),且主要关注劳动年龄人口(16~64岁人口)的教育、工作、迁移、健康、保险参与、经济活动等方面的问题。此外,部分控制变量为市级层面的宏观统计指标,相关数据来自对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
本文还对原始数据做了进一步处理,以减小测量误差。最终保留14186个个体样本、64个地级市样本。
(三)健康不平等的度量和分解
本文所研究的健康不平等是指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涉及衡量收入和度量健康的指标。对于收入指标,考虑到当期收入与健康存在内生性问题,参考Fuchs-Schundeln and Schundeln(2005)的做法,使用2012~2016年CLDS三期面板数据计算的家庭人均收入作为收入的衡量指标。对于健康指标,选择自评健康、生理健康以及心理健康三个单项指标来构建健康综合指数,并采用熵值法确定各单项指标的权重,客观全面反映个体的健康水平,以弥补单一指标在衡量健康状况方面的不足。
本文采用集中指数来度量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程度。为了分析影响健康不平等的因素及其影响大小,进一步对集中指数进行分解。基本原理是将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分解为健康对各影响因素的弹性和各影响因素不平等程度两部分。而为了分解健康集中指数,需要首先回归估计包括医保一体化政策在内的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而本文采用多期DID模型进行回归估计。此外,为了检验政策对城乡居民健康不平等的影响,进一步根据个体的城乡身份将总体不平等分解为组内不平等和组间不平等。
三、实证分析
(一)医保一体化政策对健康的影响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一方面,政策变量系数为0.0277,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医保一体化政策显著促进了参保人的健康。另一方面,农村和城市居民样本的政策变量估计系数分别为0.0243和0.0275,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从而证实了该政策对城乡居民的健康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健康不平等的分解
总体层面上,健康集中指数为0.0333,说明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显著存在。医保一体化政策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率为4.12%。此外,通过比较各因素的贡献可知,医保一体化政策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约为医疗可及性的47%、收入水平的32%。因此,相较于医疗可及性、收入水平等因素,医保一体化政策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较小。
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健康集中指数分别为0.0192和0.0350,说明城市和农村均存在“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且农村的不平等程度更高;其次,医保一体化政策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群体健康不平等的贡献分别为11.55%和2.33%,即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医保一体化政策均显著促进了健康不平等;最后,相较于农村,尽管城市健康不平等程度更低,但医保一体化政策对城市居民健康不平等的贡献更大。
进一步测算得到城乡居民健康集中指数为0.0022,说明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要好于农村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对城乡居民组间健康不平等的贡献为-0.47%,即更加公平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提高了城乡居民间健康的平等程度。但从估计系数的绝对值来看,这种贡献仍十分有限。
(三)影响机制及原因分析
在这一部分首先证实了医保一体化政策通过减轻个体的医疗负担,改善其健康状况,这一作用机制确实存在。进一步的子样本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医保一体化政策显著使得高收入者的医疗支出占比降低了2.47%,而对低收入者的医疗负担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医保一体化政策扩大了不同收入个体的医疗负担差距,从而提高了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另一方面,政策使得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医疗支出占比分别下降了2.08%和2.16%,说明政策尚未显著缩小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间的医疗负担差距,因此对缩小城乡健康不平等的贡献十分有限。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医疗资源配置失衡的现实存在性。结果发现,中国医疗资源配置存在显著的收入异质性和地域异质性,且表现为“亲富人”“亲城市”特征。在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的情况下,医保一体化政策的实施尽管提高了农村居民的保障待遇,但是并没有改变医疗资源配置失衡格局。拥有更高医疗可及性的城市居民以及高收入群体反而享受了更多的医疗资源,导致医保一体化改革对缩小城乡居民健康不平等贡献有限,且加剧城乡居民群体内的健康不平等。
(四)异质性分析——“一档制”与“分档制”
实施医保一体化政策的城市主要采用“一档制”和“分档制”两种模式。区分不同的实施模式进行分析,发现一方面,“分档制”医保一体化政策对城乡居民健康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原因在于,在“分档制”下,医保一体化政策仍然按照原城居保和新农合的缴费待遇进行档次设计,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改变参保人原有的保障待遇。另一方面,“一档制”医保一体化政策实现了城乡居民医保待遇的完全统一,且以“就高不就低”为原则进行制度设计,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其所享受的待遇水平均有所提高,从而对健康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没有起到更好地缩小健康不平等程度的作用,其原因仍在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格局在医保一体化政策实施前后没有发生改变。
(五)实施时间层面的影响异质性分析
实施改革的城市可以分为两个批次:第一批在2012~2013年实现了医保一体化,而第二批在2014~2016年实现了医保一体化。在这部分删除第二批实施城市,只选择第一批实施城市作为实验组样本,其他城市作为对照组,分析发现:医保一体化政策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且实施时间越长,政策对健康不平等的促进作用反而变大。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实施时间的增加,医疗可及性不平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释放,并超过医保一体化政策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从而使得健康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剧。
(六)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使用PSM-DID方法、更换不平等指数的计算方法(使用Wagstaff指数和Erreygers指数计算健康不平等)、更换健康的衡量指标(使用自评健康)三个维度进行稳健性检验,所得结果同样没有显著差别,从而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和可靠性。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12~2016年CLDS三期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集中指数分解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医保一体化政策对居民健康及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首先,医保一体化政策提高了医疗保障水平,显著降低了城乡居民的医疗负担,并改善了其健康状况。其次,中国存在“亲富人”“亲城市”的健康不平等。尽管更加公平的医保制度实现了城乡居民医保待遇的统一,缓解了健康不平等,但是医疗可及性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更高。在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的情况下,尽管医保一体化政策的实施缩小了城乡居民间健康不平等,但贡献有限且提高了城乡居民群体内以及总体健康不平等程度。最后,医保一体化政策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模式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其中,“一档制”医保一体化政策对健康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但会加剧健康不平等。随着实施时间的增加,政策对健康不平等的促进作用反而变大。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两点政策启示。一方面,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提升医疗可及性。国家应该加大对基层、农村健康和医疗的投入力度,同时通过医联体、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形成优质高效的诊疗体系,逐步改善医疗资源配置失衡问题,从而为改善健康平等、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奠定扎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分阶段、有步骤地落实“一档制”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在医保一体化政策实施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减小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对健康平等的负面影响,应该分阶段、有步骤地落实“一档制”。如在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给予医疗可及性相对较差的农村居民一些保费减免,待医疗资源配置公平程度提高后,再推进所有参保人缴费和待遇政策的“六统一”。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3期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